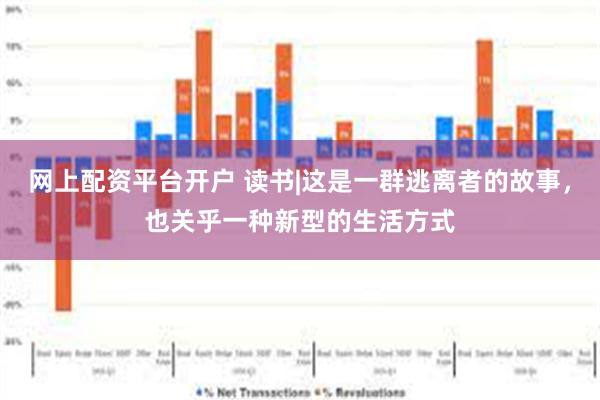
今年5月,浙江发布《关于支持高水平建设民航强省打造低空经济发展高地要素保障若干政策措施(征求意见稿)》,打造高能级空港枢纽和现代化航空产业集群,加快形成低空经济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
鹤岗,东北边陲之城,因极低的房价而频繁出现在新闻媒体头条。在鹤岗神话的背后,是一座座同样资源枯竭、经济衰退、被世人遗忘的城镇,河南鹤壁、安徽淮南、河北燕郊,以及一个个具体的、迷茫的、涌向那里的年轻人。这是一群逃离者的故事,也关乎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

《逃走的人》
,李颖迪 著
,新经典 | 文汇出版社出版
买一间两三万元的房子,囤积食物,养猫,不上班,不社交,不恋爱,靠积蓄维持最低欲望的生活,与人隔绝。从互联网的隐秘角落,到大雪覆盖的边缘小城,作者李颖迪为我们展现了人们如何策划和实践自己的逃离。
她记录了逃离者的来处——富士康工人、保安、平台客服,这些工作给人的压缩感与漂泊感,还有冷漠疏离的家庭、无法寻得的爱意;也与他们共度脱轨后的人生——在鹤岗,面对漫长的黑夜,窝在温暖的旧房子里,讨论生的意义,以及,孤独的死。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途,闯进被雪封闭的城市,走入陌生人紧闭的家,也试图探索我们这一代疲倦但仍拥有微小勇气的心灵:说到底,如何才能得到自由呢?自由又将带我们通向何方?
>>内文选读:
当我写这本书时,想起鹤岗,我首先想起的仍是那里的雪和那里的冷。不同于南方,鹤岗的雪蓬松、干燥。最初一两场,雪飘落在街道、屋顶、草地、车窗。雪在路灯下发亮。随后几天,雪慢慢融化。直到一场大雪——用当地人话说——雪“站”住了,此后鹤岗就将一直笼罩在白雪之下。雪逐渐增大,变得残暴,如龙卷风,城市严阵以待,连续的预警,铲雪车、挖机、警车四处劳作,将道路上的雪推到一旁。风中刮起烟雾一样的雪,漫天蔽日。平静时,雪又变得顽固,僵硬,冻住狗屎、烟蒂、人的脚印。街上,人们穿加厚的羽绒服、羽绒棉裤,戴防风口罩,但还是没一会儿就冻得身上疼。随着呼吸,睫毛、鼻孔、口罩里都结上一层薄霜。
这是一座与雪共生的城市。雪成为人们的度量衡,承担人们的欣喜、担忧与烦闷。伴随雪来的是如梦一般短的白日。下午3点,太阳落下,城市就陷入沉寂。这里似乎天然适合过上穴居的生活——正如来到鹤岗的年轻人所选择的生活。
2022年10月底,我从北京出发,带着一件短款羽绒服,两件毛衣,坐上前往黑龙江的飞机。鹤岗在黑龙江省北部,约有八十九万人口。网上能找到这些描述鹤岗的话:“地方政府财政重整”——2021年12月,鹤岗市政府公布取消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计划,理由为财政重整;“人口流失”——2013年至2021年,鹤岗市区人口减少幅度达17.12%;“资源枯竭”——2011年,鹤岗被中国政府列入第三批二十五座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名单。看多了这些,人们很难不产生这个印象:鹤岗,一个寒冷且遥远的边陲之地。它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没有直达的火车、高铁或飞机,多数去鹤岗的人往往选择在哈尔滨或佳木斯中转。
我飞到佳木斯,拼车到鹤岗,在高速路“南风井”卡口排队、登记信息,看着运送成团草料的大卡车来往,再坐车来到市区。旅途漫长,徒增疲惫,那会儿想去中国哪里都不容易。电话里,一个女人要求我到鹤岗之后得居家隔离。不许点外卖,她说,当然了,你可以吊根绳子,从窗外把外卖拿进来。

图源:视觉中国
我开始在网上寻找来鹤岗买房生活的人。我加入一个鹤岗的微信群聊,里头有两百多个从外地过来买房生活的人。线上群聊几乎每分钟都有人说话。一个女生说她开网店,用线上虚拟币交易。她的对白也很简单,“我不出门”。另一个女生,二十五岁,住在南边的“大陆南”小区,她是网络小说写手,最近一边写小说,一边帮人装修。一个女生画漫画,住在松鹤小区,和另一个女生相约晚上一起喝鸡汤,看恐怖片《乡村老屋》。一个女人从佛山过来,带着孩子。群里也讨论外界对鹤岗的关注。随着报道越来越多,一些人将备注改成“不在鹤岗”。
有人不断分享近期的新闻链接:
“鹤岗不是北欧”“鹤岗不是乌托邦”“去鹤岗躺平,无非又是骗你去买房”“2022年新骗局:去鹤岗买房躺平”“五万卖房热潮过后,鹤岗再次沦为鬼城”“鹤岗会重生吗?”
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低廉的房价将源源不断地吸引年轻人来到鹤岗,从而形成新的活力。
但另一个人说,人们在城市里购房,购买的只是那一套简单的钢筋水泥么?
他接着说,不,人们购买的是希望。“房价走低不可能带来希望。没有希望,这里的房价才会走低。”
还有一个男生说,无论外边说什么,他都要去鹤岗。他来自河北涿州,原来在保定一家直播运营公司做商业代播,但公司快倒闭了,他打算辞职,然后去鹤岗。“我像块橡皮,每天都在消磨。”
他写道:
感觉鹤岗就是那个样子
天黑以后就没有什么生活了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房子里待着
等待天亮
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笞,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挫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图源:视觉中国
我想到此前见过的那些房子。A家里的全套浴缸、马桶、扫地机器人,窗外的雪景,伏特加,当拒绝与外界过多来往后,家似乎成为她最后的领地,最后的堡垒。她对房子的装扮无处不在透露这样一个信息:一切为“我”所有,一切为“我”而存在。一个男人在客厅沙发上放着硅胶娃娃,这两年来她坐在同一个位置,没有挪动,他靠着她一起看电视,打发漫长时间。宁夏男人家里繁杂的健身器械与器材——来鹤岗之前你过着什么生活,到鹤岗后,你大概率还是过着那样的生活——他对我说。而现在,我坐在这个人家里,一间切断暖气的毛坯房。“我在放弃多余的一切。”他这样说。即便都选择来到鹤岗,人们的生活依旧如此不同。我很难说清其中的某些残酷性。
大约一周后,天晴,我决定不能再这样待在鹤岗的房子里了。趁着雪停,我下了楼。天空很蓝,阳光切开楼房的身体,上面是白色,下面是橙色,掉漆之处如补丁。花坛的雪变薄了,堆着一叠冻烂的白菜。路上,行人搓着手,有些忙着将雪铲到花坛里。面前是一辆货车,上面挂着横幅,“为人民加好油”。
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决定去北山公园走走。那是鹤岗一座出名的公园,在城市北部,由鹤岗矿务局修建。曾经它周边有许多冒烟、扬尘的白灰窑、采石场、白灰厂。但现在那些厂已经不见了。公园没有边界,一条长长的阶梯通向山顶。雪像被子一样盖在荒草身上,两侧是树林,大多是极高的白桦。
最初,在听说申牧的故事,还有见到他那天,以及后来我反复想到他时,我实则想弄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为什么选择过这样的生活?换言之,这个问题——后来我向来鹤岗生活的人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实则是,这种逃离,如果我们能称其为逃离的话,究竟能不能通向自由?所谓自由,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吗?就像人站在一个广场,或是一条漆黑的甬道,此刻,面前出现一些不同的分叉,像手指离开手掌那样延伸开去。分叉尽头会是什么?亮光?一片朦胧不清的雾?又或是黑暗?
作者:李颖迪
文:李颖迪编辑:周怡倩责任编辑:朱自奋网上配资平台开户